
纸上修河
—— 远离故土,此刻的我无法亲近河流,泡一杯宁红,便装下了修江,茶香四溢,尽是乡愁!
河水疯长才情,就是这条河,成就一个朝代的诗歌;
河水和墨挥毫,就是这条河,智慧的书者在挥浆的姿势中领悟书道;
河水淘尽荣耀,就是这条河,记住了陈家大屋的琅琅书声与揭榜时的暄天锣鼓。
一条河,左揽黄氏山谷,右抱陈门五杰,够知足了。


无数个春光明媚的日子,我沿着修河一路行走,青春的日子在击水声中显得殷实。幻想中的我应该素衣一袭,在颠簸的舟子上唱古老的歌谣,满岸金灿灿的油菜花,和着我野草般的方言,肆意摇曳。
河水是不倦的歌女,唱着永恒的歌,魏、晋、唐、宋,唱过神话中的黄龙,唱过古艾国中的炊烟,太祖听过,父亲听过,老家门前的那棵古樟也听过。行走是另一种形式的阅读,我在行走中阅读这条河流,或者聆听他的脉动。

河流生于哪朝哪代?融冰后的哪条沟壑诞生一个春天,也孕育一条修河?八百里幕阜巍峨蜿蜒,默默不语。我永远无法直抵河床,听河底的泥沙轻吟曼唱。或许,青铜时代的一片瓦罐,山背旧址的一块土陶,至今还沉睡河底。
照片中的景色删繁就简,在一张张取材修河的照片里,青山和流水都变得立体而富动感。在碧波之上,在时间之上,恒久的哲学与古老的谶语在光影中交辉相应,鬼斧神工的上帝导演一场场视觉盛宴。竹筏游在水中,渔民撒网而歌,雾气蒸罩晨曦,露水湿了情思,两岸青山在行走。布谷鸟啼叫的村庄,日子悠闲自得,三月采桑、五月采艾,《诗经》里的场景延续千年。
河水朝起朝落,南崖寺中的晨钟暮鼓敲醒一个个日子。日出日落,我们都是天天撒网的渔民,收获鲤虾鲫鲶,收获财情物欲,也网住一颗颗尘世的心。七百里修河诞育苍生,先民取水饮食、喂牛牧马。膜拜河水成为一种习惯:一瓢河水,洗去带血的胎衣,衍男育女,俊朗的外貌与俊俏的脸蛋映照河水;吹吹打打的道场也从一碗清水中开始,逝去的灵魂走向天国。

江南多雨,淳朴的村民祈祷风调雨顺,双手翻开日历里的二十四个节气,种菊、荷锄,赣西北经纬纵横的土地上,处处炊烟袅袅。我站在山头放歌,山花和着我的节拍,阡陌交错的乡间野菊盛开,乡人悠闲行走,小黄狗和太阳做着游戏。多情的村姑伫立河岸,河水下鄱湖、到长江,思念便到了南方工厂的流水线上。
“东南西北云为帐,春夏秋冬草作衣,终日不闻儿子哭,何时盼得丈夫归”。传说中的抱子石楚楚动人,河中的母亲怀抱稚儿,千万年的等待,河水温驯的流速把岁月拉得漫长。我无数次久久地注视这对意念中的母子,眼睛不禁湿润。一撇长江,一捺黄河,华夏大地书写一个大大的“人”字,文学中的河流和母亲紧紧相连。修河是数万苍生共同的血脉,我们是她怀中的稚儿,饮水呀呀学语,戏水欢度童年,在遍地方言声中野性成长。

星落的村庄孤单寂寞,青灯黄卷,少年的身影显得单薄。也许,970多年前的山谷先生也乘坐竹筏,在欸乃的浆声中诗意频发,跨越群山、名噪京华。羊肠小道牵着无数母亲的挂念,村前的望眼看尽秋水:你在工棚上焊接,你在教室里挥鞭,你坐在办公桌前运筹帷幄;桑叶沃若的江南有你,寒风猎猎的北方有你。“风俗尚如他日否,凭谁细问故园春。”你在千里之外,牵挂就到千里之外。
河流是流动的时间,木已成舟,沧海或为桑田,日子在白纸黑字中记载。木桨划破河的皮肤,心在涟漪起伏时躁动,取水熬药,患病的思维起死回生。雨水泛滥的年代,洪水无数次侵蚀家园,遇水搭桥,仅仅是生活妥协的一种方式。在浮桥上行走,心会渐渐不安起来,容易想起那年多雨的夏天。那些日子变得脆弱,山泉多泪,良田呻吟。上善若水,但愤怒的河流比野兽恐惧。

河流终会枯竭,我们终将老去。若干年后,河滩难见河卵石,没有了鱼翔浅底的画面,熟悉的风景只能在国画里轻描淡写,所有与河流有关的文字都显得苍白。一条河流干涸,一条静脉停止搏动!
远离故土,此刻的我无法亲近河流,泡一杯宁红,便装下了修江,茶香四溢,尽是乡愁!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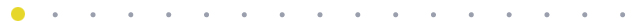
编辑:卢金鑫










